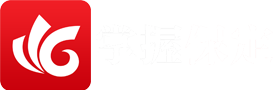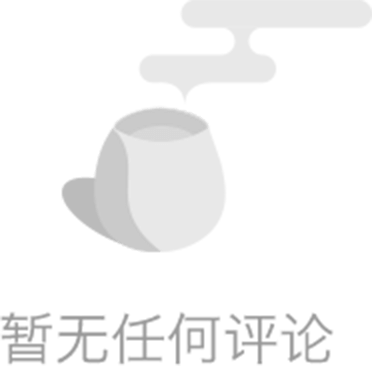记得小时候,非得天气冷得不行了人们才舍得笼炉子(也叫笼火,即生火、生炉子)。
那时常见的炉子有几种,最高级的就是圆形铸铁的,其次是木框镶砖的方形的,又大又笨,最简单的是“扫地风”炉子,就是用砖在地上直接垒个炉子,靠着墙垒,在炉子的三面挨着地儿留三个方孔,既用来通气也用来掏炉灰。如果不挨墙垒,就在四面留四个孔,因为孔挨着地,所以人们形象地称之为“扫地风”,那时学校的教室里大都是这种炉子。
不过,无论是哪种炉子,入冬之前都得把炉膛搪好才能使用。搪炉子这活儿既费力气又需技术,先得备好原料——胶泥和猪毛。胶泥得用细胶泥,不能用大块的胶泥,大块胶泥粘性虽好,但不容易和熟分,干了还容易开裂。猪毛的作用类似麻刀,如果没有猪毛,用人的头发也行。
搪炉子时要先将胶泥土和猪毛和在一起,待稀糨合适了,要用火箸(也称通条,一头呈尖状的铁棍)反复抽打,目的是将泥土和猪毛混合匀实,将胶泥抽打得细腻熟分。大冷的天,每次抡起火箸反复抽打都累得满头大汗。搪炉子最关键的一步是将和好的泥均匀地抹在炉膛里,这需要技术,一是抹得要均匀,无缝隙,保证干了不开裂;二是要掌握好炉子的内膛空间,内膛得下大上小,有肚子,有膛口,这样炉子才好烧,不易灭。但炉膛也不能太大,太大了费煤,烧不起。这就要求搪炉子的人得把尺度掌握好,既要好烧还得省煤,既要好又要巧,难啊!
搪得好的炉子,烧一段时间胶泥就都陶化了,又硬又结实,用一冬没问题。如果技术不行,用段时间就泥土开裂脱落,十冬腊月再返工搪一回,那就麻烦了,冷冷呵呵的,也受罪。
笼炉子是个脏活,炉膛里的煤快着透了得添煤,用火箸一捅,煤灰飞扬,再用火筷子夹上几个煤球或煤块就行了。这还不算什么,最要命的是晚上封火。封火时先得把炉子里的煤用火箸擞擞,擞得落下来大约三分之一,再往炉口盖上潮煤或碎煤块。封炉子时,用火箸擞炉膛里的煤时,煤灰肆意飞舞,细小的煤灰极具穿透力,即使人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,封好炉子后再看,脸上、脖子上、头发里依然是一层煤灰,吐出来的唾沫都是黑色的,如果穿的是浅色衬衣,一定会变成黑边的。这么看来现在限制烧煤、防止煤污染是很有道理的。
后来有了蜂窝煤和白铁皮做的蜂窝煤炉子,一下子就让笼炉子这活儿轻松了许多,不用搪炉子了,只要在炉子里放进几块现成的瓦就可以用了。蜂窝煤整块地添进去,烧透后再整块地夹出来,既清洁了许多又省事了许多,煤燃烧得也充分了许多。蜂窝煤真算得上是上世纪一项伟大的发明,这一发明不知惠及了多少人家、节约了多少煤。
后来的炉子样式越来越多,功能越来越先进。
现在,人们的取暖方式太多了,电暖、气暖、地热、空调,清洁卫生,省事省力,年轻人中没有几个人知道搪炉子这活儿是啥滋味了。